
曹馭博的詩集《我害怕屋瓦》並非容易讀的作品。複雜的意象、隱密的主題,以及在台灣現代詩裡相對少見、陌生的句法,都容易令人在其中迷路。
尤其《輯貳、瘋眼球》裡的九首詩,恐怕又是整部詩集裡最難懂的了。乍看任何一首詩,似乎都抓不太到主題,所用意象都像是密碼一樣,到底該怎麼解讀?
我覺得是有跡可循的。而且這些作品很有趣,是在討論詩人的創作經歷與理念(爆雷)。
👁 因為詩作很多,我只可能節錄重要的片段討論,建議大家先準備好一本《我害怕屋瓦》在手邊對照。
如何閱讀意象繁複的作品?
通常遇到意象繁複的作品,我會做幾件事:
- 先把重複出現的意象圈起來
- 從這些意象中,找一個破口
- 沿著破出來的線索,繼續推理下去
當然前提是作品本身具有邏輯結構,也願意被解讀。破口並不總是會出現。有時候如果找不到,也很可能是詩人根本就不打算給你線索。畢竟以詩作為個人世界觀,或是生活日記的密碼,也算是常有的事。
而通常遇到無法解讀的作品,我就會直接略過,承認「我看不懂」。小巷潛行守則就是寧願不懂,也不要不懂裝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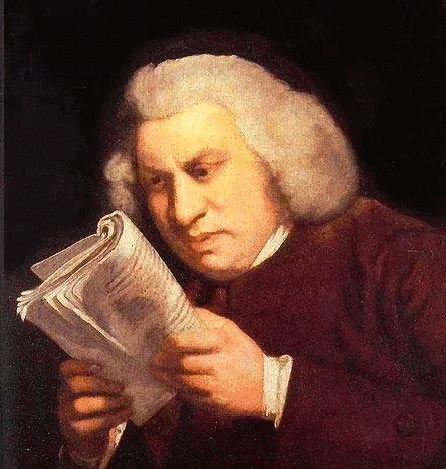
步驟一:先把重複出現的意象圈起來
首先我們把重複出現的詞彙圈出來。而因為「瘋眼球」一輯裡共有九首詩,我們的「原料」多了很多:
〈在盥洗前〉、〈四月與審判〉、〈夏日的黃草〉、〈觀看〉
▪️ 黃草葉 / 樹 / 鳥 / 雀
〈在盥洗前〉、〈四月與審判〉、〈夏日的黃草〉、〈閃光〉、〈觀看〉
▪️ 石頭
〈墜落〉、〈夏日的黃草〉、〈閃光〉、〈觀看〉
▪️ 風 / 雷
〈四月與審判〉、〈閃光〉
▪️ 墓 / 死者
〈我一無所有〉、〈夏日的黃草〉
以上是我把重複出現的意象列出來,並在後面附上曾出現的詩作。
首先注意到,我將某些意象先分類好了。這一方面是因為,我感覺它們屬於性質接近的詞彙(是的,這部分是「感覺」來的);另一方面,則是因為這些意象「出現的時機」非常接近,常常成群結隊地出現。
不過,有一些也重複出現的詞彙,我並沒有列舉在這邊,例如「藍」、「黑暗 / 影子」、「雨」。有幾個考量。其一是,如果通通列舉的話,這篇文章會超級複雜冗長;其二是,這些詞彙可能有它們蘊含的意義,但我認為對於整體的解讀幫助不大;其三,是因為像「雨」、「黑暗」等詞彙,在現代詩裡很常出現,意義多半已經固定了,所以依據經驗,我先暫時排除,以減少需處理的資訊量。
最後,大家可能已經發現了,有幾首詩作在上述表中,出現非常多次,可能代表它們蘊藏了核心概念。如果反過來排列,先舉出詩作,再數出現過幾次意象,就會呈現下表這樣:
3〈四月與審判〉:「嘴/舌」、「黃草葉/樹/鳥/雀」、「風/雷」
3〈觀看〉:「嘴/舌」、「黃草葉/樹/鳥/雀」、「石頭」
3〈閃光〉:「黃草葉/樹/鳥/雀」、「石頭」、「風/雷」
2〈在盥洗前〉:「嘴/舌」、「黃草葉/樹/鳥/雀」
1〈墜落〉:「石頭」
1〈我一無所有〉:「墓/死者」
這些就是下一個步驟,我們優先處理的對象。
步驟二:找一個「破口」
我們先看〈夏日的黃草〉——結果發現雖然出現的共同意象很多,卻似乎找不太到線索。那麼試試〈四月與審判〉?
很幸運地,在第一節就有了線索:
風雷恆——易經第三十二卦
我有兩種舌頭
我選擇一種存活
風理解全部
晦澀的兵士
躲在坑道的青年
在清晨畏懼暴亡
——體內的雀
嫩樹芽
光線抓不住河水
無岸
常青樹。
兩種痛苦
我選擇在寂靜裡
獲得全部
雷辯解了些什麼嗎?
槍聲不聽。
風——詞的薄翅
向大地澄清
雀不是我的眼睛
「我有兩種舌頭 / 我選擇一種存活」詩人在此明示:他有兩種說話方式。然而是哪兩種?這可以在最後一節找到蛛絲馬跡:
雷辯解了些什麼嗎?
槍聲不聽。
風——詞的薄翅
向大地澄清
雀不是我的眼睛
詩人在此否定「雀」,而說「雷辯解」、「風澄清」,我們大致可以確定出「雀 vs 風雷」的對立。
然而「風雷」是什麼?從詩的副標題「風雷恆」,我們翻找易經:
彖曰:恆,久也。剛上而柔下,雷風相與,巽而動,剛柔皆應,恆。恆亨無咎,利貞﹔久於其道也,天地之道,恆久而不已也。 利有攸往,終則有始也。日月得天,而能久照,四時變化,而能久成,聖人久於其道,而天下化成﹔觀其所恆,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!
象曰:雷風,恆﹔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雷與風的「變」,恰巧構成了自然法則的「不變」。詩人在此揭示:他的詩是不變而恆久變化的。
變就是詩人的不變。這或許便是《輯貳》的核心宗旨。
步驟三:沿著線索,繼續翻找
我們大致知道了「風雷」是什麼,但「雀」呢?
這時看看〈閃光〉的第二節:
只有石頭的公民
讀得懂石頭
樹上那叢
由黃草葉編織的窩
鳥群懂得居住
這是我們的第二個破口。首先,詩人將「鳥」和「樹」、「黃草葉」連結起來。有哪些詩還出現過這些意象?
——體內的雀
我照你說話的做
砍斷樹木
儘管它跳動緩慢
像死掉的太陽
我要砍斷樹木
我要砍斷
跟我一樣的樹木
歲月一塌糊塗
而我卻長著
石頭眼睛
看著天空死去
鳥兒死去
我死去
此時我們應可以確定:「黃草葉、鳥、樹」曾與「詩人」等同,存在於詩人體內;然而現在已經死去,而且是詩人急欲砍除的。
可是「黃草葉」究竟代表了什麼?上面〈閃光〉的第二節還有另一個線索:石頭。鳥群懂得居住,而只有石頭讀得懂石頭,詩人又再次將「黃草葉 / 鳥群」與「石頭」對立。
石頭是什麼?
那思想的石頭
靜止於空中
從未活過
在〈墜落〉裡,我們得知「石頭」是「思想」。則「黃草葉 / 樹 / 鳥 / 雀」便是「無思想」了。
理解至此,我們再讀一次〈夏日的黃草〉,似乎就能看出端倪:
我沒有讓步。
飛鳥在路線中
拋出靈魂
墳塚、紙
燭台的小火
我猜那靈魂
沒有嘴巴
滿口的沉默
依附在黃草上
死者的王朝
屬於死者
墳上的黃草
不屬於它們
——我沒有讓步
泥土堆在它們身上
我在上頭拔草
石頭慘綠
我不碰觸石頭
無人的墳塚
有著黃草聲響:
「這曾是我的王朝⋯⋯」
我沒有讓步;
死者的王朝
不屬於它們
儘管「黃草」曾是詩人的一部分,詩人已經〈在盥洗前〉砍除一切。他沒有讓步。沒有讓自己走回過去的自己,而是接近「思想」,成為「石頭的公民」。
這就是詩人的「變」,詩人的雷與風。他放棄了過往的舌頭,拋掉舊的寫詩手法與核心主題,轉向一種全新的面貌。
若觀察《輯壹、屋瓦》與《輯參、摘花束的孩子》、《輯肆、第六瓣太陽》、《輯伍、來回票》,便可發現詩人風格的轉向。從偏向個人與內心的主題,轉為更思想性的核心,語言也更加節制。而《輯貳、瘋眼球》在其中既是過渡,也是宣示。
正是如此,我們在一本詩集內,可以同時擁有〈我害怕屋瓦〉這樣袒露直率的內心,以及〈公園前的宇宙站牌〉這類高度凝鍊、富含哲思的作品。
我認為一個好的詩人,永遠同時關注內容與技藝。更極端地說,我認為每個詩人都該是後設詩人。關注詩之本身,正是對「寫作」此一活動的探求與敬意,也才是對身為詩人的自身負責。
附註
- 上面列舉的意象,還有一些我沒有討論到,就留待大家自行挖掘意義了。
- 我的詮釋只是我的詮釋。不一定和作者想的一樣——甚至可能根本完全沒有相關也說不定。這是非常正常的:作者、作品與讀者,本來就是三個可能有交集,但幾乎不可能完全重疊的圓圈。身為讀者,我們該做的是從作品裡,找到支持我們詮釋的證據,而完全不必考慮作者自己是怎麼說的。






